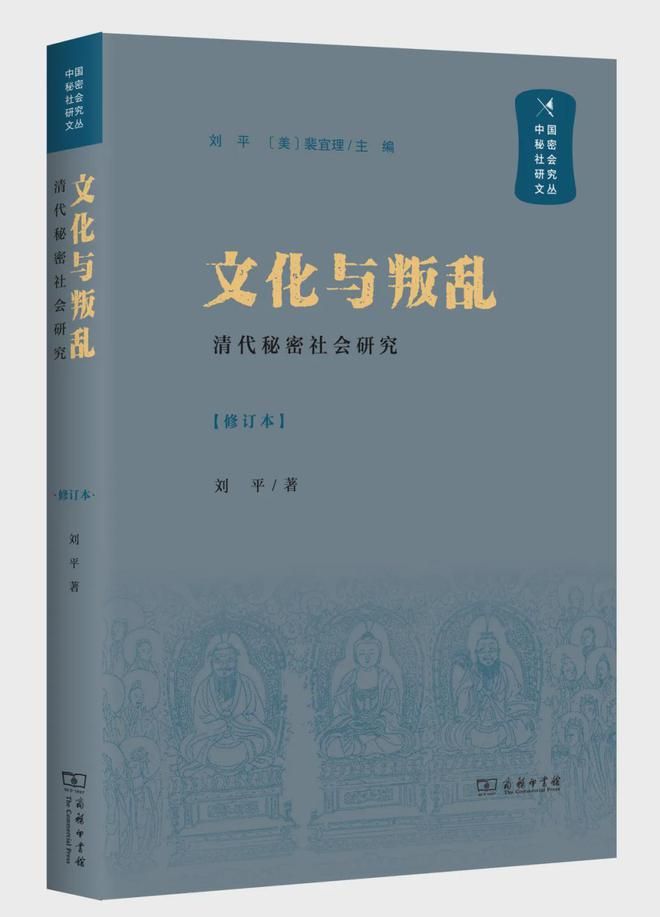
劉平 著
ISBN:978-7-100-23898-4
開本🦸🏻♀️:16開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24年7月
定價🚫:98.00元
內容簡介
本書曾於200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社會史主要開拓者之一、南京大學已故教授蔡少卿肯定該書的學術價值🧑🏽🚀,認為“把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至今本書一直是秘密社會史研究領域非常重要的一部著述。此次為修訂再版👴🏼。該書從大眾文化的角度審視清代秘密社會🏊🏽♂️,從多方面揭示秘密社會存在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土壤🩰,在此基礎上對秘密社會的反叛行為進行剖析𓀈。全書的分析始於對文化傳統的概念辨析。作者提出,“文化傳統👨🏻🦯➡️,意指文化傳承🐓,也就是以往社會流傳下來的文化在當時與現時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流變”🌒,“文化傳統的兩個顯著特點便是人民性🂠👊🏼、延續性”,此概念是在強調被視作傳統的文化🤸♀️,與近代🫚、現代、當代並沒有過多關系🩰,不完全受到社會性質🙇🏿♀️、社會製度的製約🙋🏽♂️,是可以傳承下去的,其中負面思想仍存有傳播的空間。思考“文化如何被傳承”這個問題及其深刻影響,是本書做出的最大貢獻。
作者簡介
劉平,沐鸣2平台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秘密社會史、中國近現代社會史👆。現任中國近代社會史研究會副會長、上海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老子道學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著有《被遺忘的戰爭——鹹豐同治年間廣東土客大械鬥研究》(商務印書館,2023年)、《中國秘密宗教史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等多種;譯有《華南海盜(1790―1810)》、《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等多部🤌🏿。
本書目錄
“造反有理”辨正(代序) 秦寶琦 / 1
導論 觀察與思考 / 4
第一章 民間文化與民間信仰
——中國秘密社會存在的文化土壤 / 37
第一節 宗教、巫術🥫、民俗等文化現象與歷代農民
起義的關系 / 39
第二節 巫術的源流與演變 / 47
第三節 宗教的世俗化及宗教異端問題 / 60
第二章 清代秘密教門的文化內涵(一)
——對教門寶卷、叛亂思想的分析 / 92
第一節 寶卷與秘密教門的關系 / 92
第二節 叛亂根由——秘密教門的思想信仰簡析 / 120
第三章 清代秘密教門的文化內涵(二)
——巫術🏭、符咒🦞、禁忌、氣功等現象在教門中的反映 / 148
第一節 教門中的巫術🖕🏻、魔術、法術 / 149
第二節 教門中的符咒、讖謠、乩語 / 164
第三節 教門中的禁忌🌄💳、戒律、隱語暗號 / 188
第四節 教門中的氣功、按摩👩🏿🚀🌗、武術 / 202
第四章 清代秘密會黨的文化內涵 / 221
第一節 歃血盟誓、江湖義氣對秘密會黨的影響 / 222
第二節 秘密會黨中的巫術、宗教因素 / 264
第三節 拜把結會、分類械鬥與林爽文起義 / 296
結語 歷史與現實之間 / 322
參考文獻 / 336
後 記 / 348
修訂本後記 / 350
導 論
(節 選)
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社會史研究勃興,對筆者的學術道路影響深遠📽🌄。當時🔉,“史學危機”的陰影不斷加深,社會史研究方法無疑給人們帶來了一片亮麗,提供了一條可行的途徑。從那以後,筆者便自覺與不自覺地與令人亦喜亦憂的社會史研究結緣了。
1988年,筆者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攻讀碩士研究生🎂👷🏻♀️,師從蔡少卿教授,研究近代會黨與土匪問題。在宏觀的研究視角和具體的研究方法上☎,蔡少卿老師的指導使筆者受益良多。從那以後,筆者一直在苦苦探索,其中最使我感到迷惘的是各學科之間的孤立性☝🏿,例如中國農民戰爭問題,歷史學家關心的是其過程;軍事學家關心的是戰略戰術;宗教學家認為它是宗教研究的寵兒;文學家則一味高歌農民的反抗精神。而且🧖🏽,該領域的研究,盡管成果多多,但是,“多數研究基本上是詮釋理論模式和說明公式化的規律”🍚。這種條塊分割的局面,根本不利於整個問題的深入研究,相反🍻,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史學領域“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國農民戰爭問題🪥🤛🏻,在失去“政治”光環之後,迅速陷入了“門庭冷落車馬稀”的尷尬境地。
實際上,近年來⚛️,許多學者都在呼籲加強各學科的合作,以帶動本學科研究的深入🍂。能不能換一個角度來研究歷史問題,從而在某個領域裏獲得突破呢?1996年秋🍂,筆者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師從中國秘密社會史研究專家秦寶琦教授。在與秦老師討論選題時🧳,秦老師征求筆者的意見。筆者提了三個題目,即“中國會黨史”、“清代土匪問題”和“文化傳統與清代社會叛亂”🤏🏿。前兩個,是我比較熟悉的領域🚀,後一個對我來說有一定難度🤞🏿。秦老師的答復很幹脆,就選第三個。這樣👨🏿⚖️,一個機會🤠,一次挑戰出現了🚞。
從那以後,筆者一直在圍繞選題搜集材料、思考問題🌭。隨著時間的推移,筆者感到難度越來越大,壓力越來越重。1998年6月🏜,在博士論文開題報告會上🧔🏼,戴逸⚜️、秦寶琦🧘🏽、郭成康諸教授的意見使筆者“頓悟”出許多東西𓀓,尤其是戴逸教授提出了以下幾點:
文化的分類,至少有上層文化和下層文化兩種,要註意兩者的相通之處與差異之處;
文化傳統在下層社會中沒有形成系統,但確實存在,核心之一是“義”及其相互關系;
文化娛樂在民間文化中十分重要🏏🤽🏼♂️,如“唱寶卷”,我就聽過,很好聽,是一種娛樂消遣,與儒家教育不一樣⏏️,其內容荒誕、迷信,但在道德規範等方面,與儒家是相通的;
要註意文化傳統是如何轉變為“造反”的,不能忽視農民的經濟苦難;
要區分農民起義和宗教起義🛻;
民間的教門等組織🤸🏿♂️,其思想信仰、組織、儀式等等,許多因素綜合在一起🤹🏽♀️,叛亂者利用了這種組織。
秦老師也特別強調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及其涵蓋面🙇🏻♂️。他們的指點富有啟迪🆚。由此出發,筆者將文獻資料的檢索進一步擴大到了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民俗學、民間文學等領域。
1999年6月7日上午,在經歷了緊張、充實的4個多小時後,筆者通過了題為《文化傳統與社會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委員們的肯定性評語,筆者認真傾聽👡;他們的批評性意見,我仔細做了筆錄。筆者知道,凡事不辯不明🚣🏼♂️,博士論文答辯這一環,乃是筆者的論文從幼稚走向成熟的基石。
1999年9月開始在南京大學做博士後的兩年多時間裏🛀🏽,我的任務之一就是這篇博士論文的修改⚱️、充實🫄🏼、提高。在聯系出版社的過程中,幾位資深編輯,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許醫農先生、負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東方歷史文庫”的阮芳紀先生、商務印書館的王齊博士等人👨🏼✈️‼️,從出版高質量學術著作的角度👩❤️💋👩🫶,向筆者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見。他們的意見具有指導意義。
書稿成型後🧑🏻🔧,最終確定題目為《文化與叛亂——以清代秘密社會為視角》🚺,此次修訂,定名為《文化與叛亂——清代秘密社會研究》。
本人博士學位論文題為《文化傳統與社會叛亂》,現在的書名為《文化與叛亂——清代秘密社會研究》👨🏿🏭,兩者之間有著內在聯系。
所謂文化,《易·賁》雲:“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國人歷來是將文化作為一個寬泛的“知識”概念來看待的🪱🚴🏽♂️。19世紀中期以後,世界現代化潮流奔湧💆🏼♀️,多種新學科崛起,人們研究文化的興趣持續升溫,進入20世紀,中國的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也紛紛卷入給“文化”下定義的行列。至今,國內外關於“文化”的定義已有不下200種🧖🏼。
這裏可舉中國現代兩位著名學者所作的定義,以觀“文化”這個龐然大物之一斑。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稱:“文化並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二十多年後,梁漱溟又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梁啟超認為:“文化者🤴,人類心能所開釋出來之有價值的共業也。”從他們的定義出發,我認為🛡,文化概念大約可分為兩種🦨,一是廣義的,一是狹義的。廣義者,如梁漱溟所稱🫵🏻,舉凡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無所不包”☞;狹義者👨🏻🚒,應是人類的觀念形態及其表現。後者與梁啟超所言略同。這裏,筆者無意與兩位文化大師並列,也不想躋身於給“文化”下定義的行列,僅僅是想為本書的研究內容規定一定的範圍——本書以“狹義的文化”為立足點。
什麽是傳統呢?《孟子·梁惠王下》雲🏙:“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繼”與“傳”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雲:“傳者,相傳繼續也。”關於“統”,清段玉裁《說文解字經》雲:“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傳”與“統”由單一概念轉變為聯詞概念🧏🏻♂️🐱,是取“傳”的相傳繼續和“統”的世代相承某種根本性的東西之意👰🏼♂️🙇🏽♀️。張立文將“傳統”的現代含義規定為:人類創造的不同形態的特質經由歷史凝聚而沿傳著、流變著的諸文化因素構成的有機系統👣。在現代漢語中,“傳統”可作名詞,也可作形容詞,張立文顯然是將其作為名詞來加以解析的⏭🎗。
用作形容詞的“傳統”指的是過去的、消逝的意思,把它來與文化搭配,就是傳統文化。在生活中、研究中👵🏽,人們更常使用的是“傳統文化”。那麽🧎,我為何要用“文化傳統”呢👨🍳?首先🎅,據朱維錚稱🏞⏱,歷代相傳的文化,大致可分為死文化和活文化🤵🎇。凡在歷史上存在過、興旺過,但在現代社會文化生活中已消逝的傳統👨🏼🦱,如“瑪雅文化、金字塔文化和中國的銅鼓文化、西夏文化等,屬於死文化,相反🥷,先輩們曾經認定是合宜的行為規範,以後繼續被認為合宜,在現代生活中依然存在,盡管已經變了味並且變了形👩🦼,那就是活文化”👩🏻🦰。
筆者認為,死文化🦸♀️🧙🏻♂️、活文化的概念提得很好🟩,至於前代流傳下來的文化的“合宜”性,則不敢苟同👩🦯➡️,因為“人以群分”🍊,此群認為合宜者,彼群未必認為合宜🤒👈,如跨入民國後的張勛👨🏻⚕️👨🍳、袁世凱腦子裏的皇權思想,從古及今中國社會中的迷信🧑🦰、溺女🫱🏽、械鬥等現象,當然都是不合宜的。
其次🦸🏻,綜合前述,本文的“文化傳統”意指“文化傳承”🤦♂️,也就是以往社會流傳下來的文化在當時與現時社會生活中的影響、流變。
這裏還要對“上層文化”“下層文化”和“大傳統”“小傳統”的問題作些分析。人類學家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1897—1958)在其1956年出版的《農民社會與文化》一書中👿,提出了“大傳統”(Great Tradition)與“小傳統”(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大傳統”是指“一個文明中,那些內省的少數人的傳統”🤾♂️🏇🏽,“小傳統”則是指“那些非內省的多數人的傳統”🥋🔄;“大傳統是在學校和教堂中培育出來的🈲,小傳統則是生長和存在於村落共同體文化中”👨🏽⚖️。這裏,雷氏顯然是將“傳統”與“文化”融為一體的🏄🏽♂️。因此♥️,其“大小傳統”之分與以下一些概念如“高度文化和低度文化”“高雅文化與平俗文化”“神聖文化與世俗文化”等在意義上相近。
雷氏還認為,在有些文明中,這兩種傳統是很難區分清楚的。如在原始部落中,甚至可以講沒有大傳統。而在兩種傳統可以區分的文明中🥲,如中國和印度🏄🏻,大傳統與小傳統是互相影響的🧖🏽,主要表現在正統的哲學、宗教等精致文化向地方流動,逐步“地方化”(parochialization)🙍🏿♂️。我在研究中發現,上層和下層文化也是互相影響的,有些下層文化後來逐漸上升為上層文化(如“道教文化”、如上古民間詩歌演變為《詩經》)🧋,有些上層文化也可變為“下層文化”(如“唐武宗滅佛”以後的佛教、摩尼教)🧏🏼♀️,更多的則是隨著時間、環境的變化而互相消長。問題是🕠,下層文化對於學界而言,還是一個少有接觸或接觸不深的領域。
“叛亂”一詞,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國內史學界研究農民反抗問題時是基本不用甚至是持批判態度的。正如美國學者穆黛安(Dian Murray)所指出的: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學者對於大部分國內動亂一直都抱著一種僵化的觀點。結果🤸🏻♂️,那些說法誇大了民眾運動的自覺性以及思想啟示作用。
日本的歷史學者往往用“反叛”、“叛亂”🦔、“反亂”等詞,意義相同。西方史學界,使用比較頻繁的是rebellion,即造反🧜、叛亂、反抗之意(國內一般譯作“叛亂”),另一個相近的詞是revolt(造反、起義、反叛之意)🚣♂️,帶有正義性的起義用uprising(起義🌲、暴動之意)🙍🏼♂️,一般的反抗用protest(有抗議、反對之意,如“鄉村民變”,在英文中便是rural protest)🧳,騷亂用disturbance👩🏻🍼、暴亂用disturbance或riot。我們在研究農民反抗問題時忌諱使用“叛亂”一詞🌵,並不在於“叛亂”的字面含義,而是在於特殊時代造成的政治含義。正如筆者在與人討論博士論文題目的一次私人談話中所受到的質問一樣:“把農民起義視為‘叛亂’, 這不是站在封建政權的立場上講話嗎🤾🏼♀️?”
但筆者仍然堅持己見,希望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來使用這個詞。正如美國邪教問題專家瑪格麗特·泰勒·辛格(Margaret T. Singh)所說🪹:“不論某些邪教組織的行為如何招致外界成員的非議🦛,‘邪教’一詞本身不過是個描述性的詞匯,並無貶義。”仔細思考一下,用“叛亂”是比較恰當的🚴🏼♀️,它所評價的不僅是有遠大抱負的農民領袖,還包括有私欲、有野心的首領🤺;不僅指稱正義性的農民起義🚱,也包括純宗教性起義、盜匪起事、民變🔩、地方騷亂、暴亂等性質各異的動亂。無論正🏌🏽♀️、反🧖🏼,都對封建統治秩序構成了威脅。
換言之,現在報章及法律指稱當代新出的(包括外國的)異端教派(heterodox sects)或膜拜團體(cults)時都開始使用“邪教”一詞,而“邪教”的正式出處是封建統治者,如嘉慶皇帝的《禦製邪教說》即是,他是針對發動川楚大起義的白蓮教說的🎨,我們現在順手“拿來”,大概沒有站在嘉慶帝立場講話的含義吧。所以,與“農民戰爭”“農民起義”“農民革命”這類詞組比較而言,本書使用的“叛亂”是一個中性詞。
從政治學角度來說,“叛亂”所包含的範圍比較寬泛,如民族叛亂🩱、宗教叛亂、統治階級內部派別的叛亂(諸侯叛亂、宗藩叛亂)等♊️。本書主要探討的是以清代秘密社會為主要力量的農民為什麽走上反抗道路的問題,以當時的社會狀況及其變遷為考察依據⛈👨🏿🦲,所指“叛亂”的主要內容有農民起義、秘密社會起事🫱、盜匪起事🤯、民變🦀、民眾騷亂(如械鬥)等,故又曰“社會叛亂”,而行文中應用最多的可能是通俗的“起事”“起義”“造反”等詞。
現在🎿,本書名定為《文化與叛亂—清代秘密社會研究》🧎🏻♂️➡️,原因有二:一是為了簡單明了起見👮🏽♂️;二是副標題已然勾勒出本課題的研究範圍,“叛亂”之前沒有必要再加“社會”一詞。當然🍝🤸🏽♂️,在具體論述中,“文化傳統”“社會叛亂”仍是常常要用到的🙎🏽🧑🏿🔬。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本書主要以清代秘密社會為對象來探討文化與叛亂的關系🚴🏻♂️,剖析清代秘密社會生存💨👬🏻、發展、反抗🕴🏼、演變的文化土壤👩🦳,尤其是影響其思想信仰的文化因素,從而揭示農民反抗的深層原因🍢。在此,有必要對“秘密社會”這一概念做些解釋🚴。
中國秘密社會史是歷史學中一個十分艱深的領域,它以活躍在中國歷史上的為數眾多的秘密結社為研究對象💆♀️。
一般來說,秘密結社是指那些具有秘密宗旨或教義、按照嚴格的秘密儀規從事地下活動的下層民間團體,由於各種秘密結社都是在秘密狀態下進行活動,因而構成了一個外人不易了解、官方不易控製🧉、正常社會秩序難以容忍的民眾糾合體🙎♀️,人們通常稱之為“秘密社會”。
秘密結社有以下三個特征:
1.非法性💉。由於它所奉行的秘密宗旨或教義對抗官方意識形態,其活動也不受官方約束🍉,所以為法律所禁止🌶,只能非法存在。
2.神秘性。秘密結社都有自己的入會入教儀式、聯絡方法和賞罰規章,這使它具有極大的凝聚力和保密性🤶,其特異的隱語💛、標誌🎹、口號及其傳授方式等,很難為人識破。另外,秘密結社所選擇的崇拜偶像,來自宗教、神話乃至傳說中的英雄豪傑,加上施符上表、吃齋誦經或開山立堂、結盟拜會等似教非教的方式,令人神秘莫測🧑🏿✈️。
3.反社會性👍🏼。秘密結社的基本信眾大多為破產農民🕰、城市平民、手工業者👮🏼、商販🤹♀️、運夫💔、船民🧖♂️、水手乃至僧道醫蔔😲、散兵遊勇🙎🏻,一方面他們抱成一團,相依為命,具有互助意義🧗♂️;另一方面,這類人良莠混雜,不少人桀驁不馴🥰,常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壞性。
秘密結社的異端思想和非法活動🏄♂️,尤其是經常反抗政府的起義🍝🐕,對王朝秩序構成很大威脅👝。歷代政府莫不從法律上加以禁止💇🏽♂️,從軍事上加以鎮壓。此外,秘密結社成員為生計所迫,除了進行正當的經濟鬥爭外📳🚅,又往往呼朋引類、劫掠窩贓⛷、欺行霸市🦩,直至殺人越貨。因此,秘密結社的活動對正常的社會秩序有很大的破壞作用。對於他們的活動,我們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千萬要避免或捧上天、或摜諸地的做法。
清朝是一個秘密結社空前繁多的朝代。根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檔案的記載,清政府統計出當時的秘密結社名目有215種,其中清政府立案偵查以至於留下檔案可查的就有111種𓀃。有人估計清代秘密結社總數不會少於三四百種。
對清代秘密結社的分類🕤,一向有“南會北教”之說。“會”是指會黨,以天地會為主體,活躍於福建、臺灣、兩廣和長江流域一些省份。小刀會👩🏼🚀、三點會、三合會、哥老會、仁義會、江湖會等名目是它的支派📽。“教”是指教門👵🏿,流行於中國北方各省👊,例如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義和拳、一貫道、大刀會、紅槍會,等等。這種劃分很粗糙,且不說清中葉以前教門之獨領風騷,即使是在清季至民國,南方之教門,北方之幫會📐,都是有著極大勢力的。盡管如此🚿,我們可從這一角度窺見清代秘密結社分布的大致情形👩🏻。
